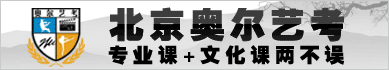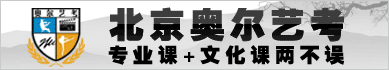看了纪录片《最后的山神》感受颇深。序幕从春节过后的第一个早晨拉开。在中国东北部大兴安岭的鄂伦春族孟金福仍然过着游牧生活,靠狩猎生活但是大多数人已经永远地结束了狩猎生活,居住在了山下的定居点。而孟金福,则依然保留着最原始的生存方式,信奉火神、月神,万物皆神,尤其是信奉山神,相信是山神给了他猎物和住所。孟金福在很多树上雕刻了山神的摸样,对他膜拜。本片忠实记录了这些鄂伦春人的最原始的生存方式,尤其是他们制作桦皮船的工艺,但是随着这些老鄂伦春人的逝去,古老的传统就渐渐遗失了。
《最后的山神》表层记录了大兴安岭鄂伦春人孟金福夫妇在山林中的生活,内在却“自始至终形象地表现了一个游牧民族的内心世界”——“以自然万物为神灵,日月水火,山林草木,都可以成为他们膜拜的对象。”
细节可以说是所有影片的重要环节。该片最突出的就是对动作细节的运用,着重塑造了主人公孟金福,以他的一板一眼一言一行形象的刻画了这位鄂伦春族游猎者,突出了他的纯朴、善良、真诚营造了他的原始气息。影片按照时间和空间顺序层层展开描绘,结构严谨叙事清晰情节真实感人,无不表现了孟金福纯朴,善良,真诚的一面。孟金福作为鄂伦春最后一位萨满,他的行为中必然带有很多原始宗教崇拜的痕迹,也就是把大自然的万物都看作是神来崇拜。比如:虔诚地在松树前雕刻山神,并顶礼膜拜;每次进山打猎都要请求山神赐予他猎物;当打猎有所收获时,他就认为这是山神的意思,便要虔诚地给山神进贡祭品。有时没有祭品时就给山神点根烟,这些细节都是人物性格的外化。孟金福老人身上的很多传统反映了鄂伦春人的心灵。比如:孟金福老人的猎枪老了,老的很不容易找到同型号的子弹;他在打猎中坚持不用套锁和夹子打猎,反映了鄂伦春人不“涸泽而渔”、保护生态环境、爱护生命的品质;他捕鱼时用大眼渔网的动作细节,反映了他内心的善良;当它割树皮时不伤树干,不正反映了他对大自然的爱吗!物件细节比如:马尾上的红布带、猎枪上的红布、松树上雕刻的山神像等等,反映了原始的宗教崇拜。捕鱼前女人用来打男人的柳条,表明了鄂伦春人独特的风俗和情感表达方式。刮胡子的匕首、跳绳用的萨满鼓,都是老萨满古朴遗风的物化象征。
纵观全片,在画面细节的用光上也颇有特点,尤其是大量逆光的使用,不少镜头还把太阳包含在画面中形成眩光的效果。运用这种手法的目的似乎很显然,就是要体现山神在孟金福心中权威神圣的地位。然而摄影师并没有止步于此,根据主人公所处的不同情景,所拥有的不同
心情,相应对“逆光”这一技法作出了恰当且出色的变化。金黄的色调,巨大的太阳,舞动的剪影。在黄昏下
表演萨满跳神这一段落中,摄影师利用夕阳特有的方向和色温,借着最后一次萨满跳神暗示神灵的远去,更渗透着鄂伦春人对民族没落的无奈与悲凉。一棵雕有山神的大树被砍伐了,摄影师把孟金福“有一种自己被砍伐了的感觉”体现为大面积沉重的低调,孟金福夫妇坐在山坡上,两个人沉重的剪影贴在低暗的天空上。从天空透出的那一丝光线便是逆光的光源,似乎山神的光已经不能普照在他们的身上。主人公的失落感尽在不言中。
定居以后鄂伦春人已经不再在正月十五祭月神了,而孟金福却执着地坚守一贯的传统,深信此时月亮神仍然在天上望着人们。微弱的月光,撒在孟金福的胳膊上形成隐约的轮廓,低调的逆光运用,正是大量的细节丢失和黑暗中微光的点缀,使画面弥漫着一种原始却神秘的宗教色彩。
逆光可以说是全片光的运用的骨架,不仅可以突出被摄主体,还支撑着全片的光影基调,着重把各种“无形”的神通过逆光加以表现。而对于日常生活的其它细节的刻画,光的运用依然起着重要的作用。其中一种用光技巧就借用了自然的“道具”——雾和烟。
孟金福妻子在住处煮食所产生的烟,一方面描写了他们的日常煮食这个细节,另一方面利用烟的大气透视效果把从顶上照进来的太阳光显现出来,或许是在暗示住处的简陋,从而体现孟金福夫妇执着的信仰,又或许是在暗示神明在他们头顶守护。无论摄影师的意图是什么,没有烟这一“道具”的话,整个场景就会变得索然无味。
从语言细节上来说,全片的点睛之笔就是解说词中的一句话“在孟金福(老一辈)的眼里,山林是有灵魂的;而在郭保林(年轻人)的眼里,山林就是山林。”这些细节的对比,反映出两代人的巨大差异。
可以说《最后的山神》具有较大的艺术价值,首先它的真实性就是历史地再现,教育的典范另一面揭示了民族的变迁,没落不仅仅是族人生活方式得变化,更是一种文化在世界各种大潮的冲击中的消失,与昌盛。
任何
作品不可能都十全十美,多少会有些瑕疵,本片中孟金福在渔船上的时候说:“女人打男的一下,今天就有运气,不能空手回来”这句话说得给人一种些莫名其妙的感觉,我们虽然知道是摄影师问的,但突然出来这么一句话略显仓促。但无论从主题,人物刻画、细节描写还是艺术价值上来说都是很不错的,可以说是纪录片史中的典范。